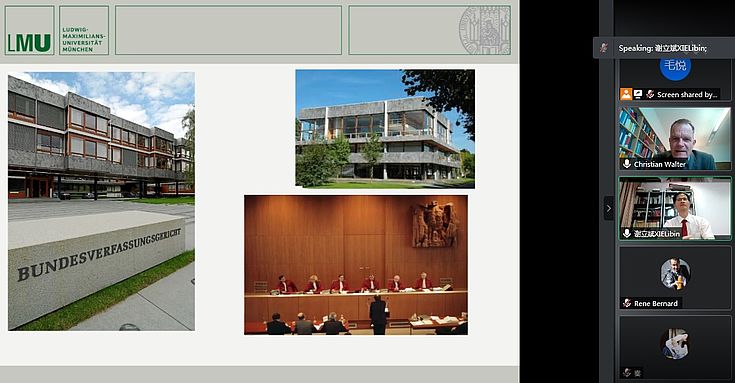应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邀请,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克里斯蒂安·瓦尔特教授和巴伐利亚行政学院前院长约根·哈贝西博士分别于2021年5月20日和6月17日进行了线上讲座,讲解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背景和联邦国家原则。随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院长谢立斌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赵宏教授发表评论并谈到了中国制度的具体特点。最后,听众就讲座内容提出问题,专家们予以解答。
与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线上学术讲座
“联邦宪法法院与德国的联邦国家原则”
联邦宪法法院:主要诉讼类型
以美国最高法院于1803年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确定联邦法律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为例,过去曾在联邦宪法法院担任研究助理的瓦尔特教授,从历史和比较视介绍了联邦宪法法院的主要诉讼类型。他详细介绍了规范审查(抽象规范审查和具体规范审查)、机关争议、联邦与州的争议和宪法诉愿四种诉讼类型。
在规范审查中,联邦宪法法院既审查不与具体案件相关的法律(抽象规范审查),也审查与具体真实的法律案件相关的法律(具体规范审查)是否符合宪法。在具体规范审查中,各专门法院进行分散的初步审查,但联邦宪法法院作出集中的裁决。关于抽象规范审查,瓦尔特教授特别强调了其在实践中的对抗性特征。这意味着有权提请审查的机关可以主张其机关权利受到了侵害。这在联邦与州之间或个别州之间的争议中都有可能出现。
联邦宪法法院很少审理联邦与州的争议,机关争议是其另一个活动领域。值得强调的是,议会党团也可以作为争议一方。最为重要的诉讼类型是宪法诉愿,任何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人都可以提出宪法诉愿。讲座第一部分的最后,瓦尔特教授解读了过去五到十年的统计数据,数据表明,所有诉讼类型的总数稳定在每年5000-6000件,其中大多数都是宪法诉愿,但只有1-2%的案件最终胜诉。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瓦尔特教授谈到了宪法法院与分权的关系。他特别讲到了所谓的“反多数难题”,即由非经选举产生的司法机关废除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的决定的问题,尽管法律为法院设定了限制,但仍应批判性地看待其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在司法领域,专门法院的任何裁决如果违反宪法均会受到宪法法院审查。而与行政部门的互动则基本上不受质疑,这方面的司法审查在实践中也非常普遍。
总之,一方面,联邦宪法法院是法律参与者并因此受到限制,其不能主动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对很多问题作出裁决,因此也是事实上的政治参与者。
在随后的讨论中,在回答赵宏教授的问题时,瓦尔特教授举例说明了联邦宪法法院食品“集装箱”案裁决背后的逻辑。当被问及公众舆论对法院的影响时,瓦尔特教授指出了法院的“独立性”,过去的判决和公众的激烈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95年澄清教室不应该有悬挂十字架的义务的“十字架判决”。
在德国具有悠久传统的联邦制
在6月17日的讲座中,哈贝西博士首先梳理了德国联邦国家原则的历史:除了纳粹时代,德国及其前身国家采用各种形式的联邦制已有150年之久。1949年之后,最初只有西德是联邦国家,而在统一后,整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采用了这一制度。
但这个词的法律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联邦国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联盟,其中国家联盟和其成员都具有国家的法律性质。因此,联邦国家是由其各个成员州组成的国家。联邦通常被称为中央国家,其与各成员州一样,直接对成员州的成员行使主权。所以,生活在联邦国家的人们直接受到两种国家权力的影响:联邦权力和一个成员州的权力。在联邦制国家,一部整体国家宪法在联邦和各州之间分配国家的全部任务和权力。
通常情况下,除整体国家人民代表机构外,联邦国家还有一个联邦机构,即所谓的第二院,其任务是代表各成员州的利益。在德国,16个州的政府在联邦参议院中都有代表。通过联邦参议院,各州参与联邦立法的权利得到保障。大约40%的联邦法律需要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同意法律)。在其余情况下,联邦参议院只能对联邦议会通过的法律提出异议,但联邦议会可以否决(异议法律)。
根据《基本法》第30条,只要《基本法》未作出其他规定或未允许作其他规定,行使国家权力和完成国家任务是各州的事务。因此,如果联邦想要采取行动,其必须以《基本法》的具体规范为基础。如果联邦没有权限,就总是由各州负责。
立法权的主要焦点在于联邦。《基本法》第73条列出了约二十个联邦拥有专属立法权的领域,如外交事务、国防事务或护照制度。
《基本法》第74条将三十多个领域的共同立法权分配给联邦。这意味着,各州只有在“联邦没有通过法律行使其立法权的情况下”,才能在相关领域行使立法权(《基本法》第72条第1款)。对民法、刑法和外国人居留、居住权,就适用这一规则。
如果《基本法》没有规定联邦的立法权,那么立法权属于各州,《基本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各州专有的立法权。联邦国家原则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为人们认为,分散的行政比集中的行政更能作出适当的、贴近社会实际生活的判断(“行政联邦制”)。
司法权也在联邦和各州之间作出了区分。在此,联邦最高法院是各州法律诉讼的上诉机构,从而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因其进行诉讼的州的不同而受到影响。
支持联邦制的论点
联邦制的适用有各种充分的理由。例如,辅助性原则假定,不得剥夺个人可以自主承担的事务而将其交由集体。但如果个人需要,集体有义务提供帮助。这一思想也作为一项结构性原则被运用到国家组织中。
在联邦制国家中,国家权限在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划分,因此联邦制也起到了纵向划分权力的作用:它防止官僚机构过度统一,从而加强了对自由保障的横向的权力控制。在州的管辖范围内,各成员州可以自主发展,并以这种方式与联邦国家的其他成员竞争最佳解决方案(竞争性联邦主义)。此外,联邦模式为政治少数派提供了更多机会。例如,如果一个政党在联邦层面做了多年反对派,它也还能继续参与州一级政府,从中获得更多经验和信心。
国家的基本秩序也必须能够对国家社会或科学技术的经验和新发展做出反应,因此,在修改宪法(基本法)的可能性方面,德国的联邦制也很重要。为此,《基本法》要求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对宪法修正案作出一致的决议,并必须以特定多数(两院均达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不过,《基本法》从纳粹过往中汲取了相应教训,明确规定了立法机关修改宪法的限制:《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规定,不允许对《基本法》的修改影响联邦对州的划分、各州对立法的基本参与以及第1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和第20条(民主和社会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中规定的原则。
中国-——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还是只是相对有差异?
谢立斌教授强调,德国的联邦制度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柏林和勃兰登堡合并的尝试(最终失败)。在1949年,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最初也曾有建立一个联邦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但后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协商,中国没有这样做。不过,联邦制因素在中国也有体现。一个例子是在新的经济、行政管理模式或改革开放中制定试点方案的做法,这些方案通常首先在较低的行政级别层面进行尝试,如果成功,则扩展到整个国家。在税收制度中也可以看到联邦主义的一些特点,某些类型的税收收入使各省受益,允许它们有一定程度的财政独立性。少数民族自治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有联邦制结构特点的例子。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则更进一步,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以外的诸多领域具有自主性,享有一定自主权,包括有权发行货币。赵宏教授也强调了联邦原则在德国的重要性。辅助性原则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尤其是在疫情时期。例如,不同的省份和城市往往采用不同的防疫措施。
与谢教授一样,赵教授也强调,虽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利用了联邦制的因素。因此,赵教授认为,中央国家和联邦国家的区分始终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问题。
作者:奥乐
翻译:谢立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