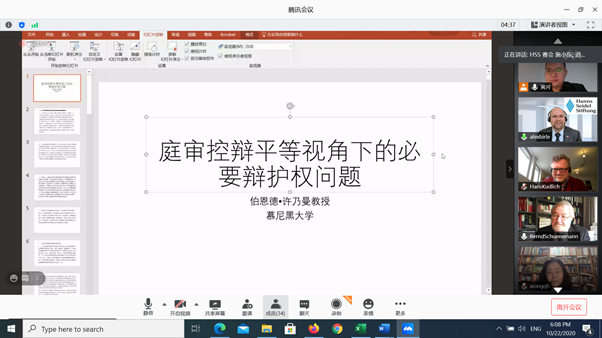被告在庭审中享有辩护权,这是法治国家无可争议的根本原则之一。然而,不同国家辩护律师的权利与义务范围也有所不同。在本次网络研讨会上,德国慕尼黑大学贝尔德·许乃曼教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斯·库德里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教授共同就中德两国在此方面的不同之处及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庭审控辩中辩护权的保障与必要限制问题
与中国政法大学的网络研讨会
目标:公平的控辩平衡
许乃曼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庭审控辩平等视角下的必要辩护权问题”。首先,许乃曼教授介绍了庭审中控方(国家检察机关)与辩方(辩护人)作为对立两方的法律背景及历史背景。为实现查明事实真相的庭审目标,避免触发惯性效应,即法官在审理前无意识地受到既有检方证据材料的影响,辩方的地位必须足够强大。单是从“自然法角度”来看,强有力的辩方也必不可少,因为在刑事诉讼中几乎不可能仅仅依靠精准的自然科学手段证明罪责,而是需要采用证人证言等不可靠的证据手段,因此以实证认识论为基础便可推导得知有效辩护参与的必要性。然而,控辩双方的地位在一开始便已十分明晰:与拥有检察院等诸多机构的国家相比,辩方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许乃曼教授认为,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平等武装原则并不存在。尽管如此,为了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控辩平衡,辩方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其中便包括卷宗查阅权。在德国,辩方被允许查阅卷宗,而不必透露辩护手段。其他手段还有证据申请权、呈示己方证据权、申请法官回避权。然而在许乃曼教授看来,在诉讼实务中,辩方询问证人却并无实际效用。原因一方面在于前述的法官惯性效应,另一方面在于证人询问顺序,即仅当法官与检方询问完毕后,辩方才能够询问证人。同样,“最后陈述”权在诉讼实务中也几乎无甚意义。
限制与正确应对辩护权滥用问题
当然,辩方也可能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虽然实践中这种情形更多见于法官)。库德里希教授认为,拒绝权、提问和解释权、证据申请权属于极“易受到滥用”的权利。许乃曼教授建议创设一个裁定权利滥用问题的独立“司法庭”,库德里希教授在其题为“辩护权滥用情况下的必要限制问题”的报告中便恰好谈到了这一点。证据申请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告甚至辩护律师可以“严重滥用”这一权利,无理提交无数次申请,其目的并非澄清事实,而是拖延阻挠案件审理。但由于刑事诉讼始终伴随着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必须要使之达成合理平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容忍这一行为。然而,若诉讼权利遭到利用,导致权利赋予所追求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那么便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法院是否一定不可能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滥用应对”)?针对个案作出精准权衡十分困难,且很难保证客观。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德国《刑事诉讼法》仅针对某些滥用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他情形下则需要以其他法律法规为基础作出应对,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14条及第226条规定的诚信原则。若在具体情况下确实出现滥用行为,必须核查目标的违反是否达到了能够认定不合理行使诉讼权利的程度。在认定目标的违反情况时,裁决的具体基准必须是各项相关权利的目标。在选择如何应对滥用行为时,应区分是驳回行使某项权利,还是禁止今后继续行使这项权利。选择时还要考虑到,仅是某项权利的行使构成“滥用”,还是整个“行使行为”构成滥用。对法官之拒绝权是一个防止权利滥用很好的例子,此时适用两级保全制度:第一级是《刑事诉讼法》第25条第1款对可能提出的申请进行预防性的时间规定,第二级则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a条规定,从形式瑕疵、拖延诉讼、目的与诉讼无关等多个滥用角度出发,更易对拒绝申请予以驳回。在驳回“受到滥用”的证据申请方面,2017年及2019年版的《刑事诉讼法》更是作出了大幅扩展。
与许乃曼教授一样,根据实际经验,库德里希教授也同样认为,辩护权的滥用并非普遍现象。今后在处理权利滥用问题时,必须始终牢记“诉讼程序经济性”决不能优先于被告利益。
“法官回家卖红薯”
熊秋红教授指出,中国的情况与德国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中国,力求实现控辩平衡也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法官及国家拥有的权力,辩方目前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熊教授列举了中国几个有名的“死磕派律师”滥用辩护权阻挠案件审理的例子。为贬低法官,更有甚者抛出了一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真的送给了法官一袋红薯。但与德国相同的是,一般来说,在中国也是法官拥有更大的权利,“平等武装”同样是无从谈起。由于存在惯性效应,在中国,辩方查阅卷宗对审判结果的实际影响也甚是微小。法官回避及最后陈述同样收效甚微。
作者:奥乐·安吉哈特
翻译:毕丰皓